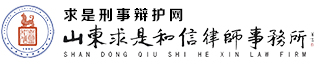从一起贪污案件的成功辩护看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辩护中的实际运用
作者: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刑事法律事务部 李宗习律师 邹怀辉律师
近日,笔者辩护的一起贪污案经过一审、二审、发回重审,最后检察院撤诉后撤销案件。该案涉案数额并不大,但司法机关认定犯罪的思路和辩护人辩护的思路还值得探讨一下。简单一写,仅做引玉之砖。
李某某自2003年3月至2009年9月担任事业单位某办出纳。其给某办会计出具借条,借支公款,用于给某办工作人员发放工资、加班费、过节费等,凭经领导签字的支出凭证等同会计结账。市审计局在2011年对某办进行审计时,发现李某某管理的现金账目出现11万余元的短款。后李某某采取伪造领导签名、使用虚假票据报销,票据重复报销等手段同会计平账。被发现后,除一部分差额李某某能说明去向且有证据证明外,余款6.6万元不能说明去向。2013年7月,检察机关对李某某贪污案立案侦查。第一次讯问时,李某某承认上述款项被自己用于个人支出了。此后便改变供述,辩称所有款项已为公支出,短款是因自己未妥善保管支出凭证,也未详细记录支出情况所致,否认自己侵吞公款。2014年1月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指控李某某采取伪造领导签名、使用虚假票据、重复报销票据等手段,对侵吞的公款进行平账,侵吞公款6.6万元,直到案发一直非法占有上述公款,构成贪污。案件审理期间,辩方又提供证据,证实该6.6万元已为公支出。但一审法院只认可其中的4.3万元用于公务支出,余款2.3万元被用于公务支出证据不足,构成贪污罪。李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审理期间,检察机关撤回起诉,以法律发生变化为由撤销案件。
如果辩方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该2.3万元被用于公务支出,李某某自然不构成贪污罪。这涉及刑事证据的运用及事实的具体认定问题,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虽然检察机关做出撤销案件决定的理由是法律发生了变化,2.3万元已达不到贪污罪立案的标准,但如果这个数额是3万元以上又该如何呢?类似案件,若按检察机关的指控思路,辩方想要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涉案款项被用于公务支出,通常比较困难,可能会落入检察机关的“圈套”。而从无罪推定原则的角度,则可以回避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涉案款项被用于公务支出的风险,直接否定检察机关的指控思路,将涉案款项未被用于公务支出的证明责任抛给检察机关。
社会生活中,以行为人实施贪污行为(也可能涉嫌职务侵占等犯罪,结论具有一致性,这里只以贪污为例)时是否已合法占有(民法意义上的占有)公共财物为标准,笔者将其行为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形
1、以非法手段取得公共财物,占为己有,或用于公务支出、社会捐赠。
2、以合法手段取得公共财物后,又采取侵吞、窃取、骗取等手段,将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或者用于公务支出、社会捐赠。
3、以合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后,无法查明行为人有贪污的故意,而行为人也无力证明财物的具体去向,又不能排除公务支出的可能。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我们可以看出,行为人基于贪污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后,贪污已经既遂,赃款赃物的用途不影响贪污的认定。但做出这样认定的前提是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就是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所以,对于第1种和第2种情形,认定为贪污应该没有争议。需要注意的是第1中情形中,行为人在贪污故意的支配下将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第2种情形中,行为人首先合法占有公共财物后,又在贪污故意的支配下将公共财物非法占为己有。
对于行为人将其占有的公共财产用于公务支出或社会捐赠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区别对待:如果能够证明行为人在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时是出于贪污的故意,可认定为贪污;如果不能证明行为人在非法占有单位财物时出于贪污的故意,而其又以单位出资的名义用于公务支出或社会捐赠,可不认定为贪污。
对于第3种情形,笔者认为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不能认定为贪污。
无罪推定最早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当然,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度的设计看,并非全盘吸收西方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设计的刑事诉讼制度。
无罪推定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推定,无须基础事实即可证明无罪这一推定事实的存在。换言之,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
贪污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故意,客观上有使用侵吞、窃取、骗取等方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这种行为应当是在主观故意支配下的一种积极的作为,而不是消极的不作为。所以,要指控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贪污罪,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控诉方至少要证明两点:一是行为人有贪污的故意,二是行为人实施了贪污罪的具体实行行为,并将财物占为己有。但第3种情形中:
1、控诉方无法证明行为人有贪污的故意,更无法证明行为人贪污的故意产生于何时。
2、控诉方无法证明行为人实施了何种贪污罪中的具体实行行为,也无法证明公共财产已被行为人占有。
所以,此种情形不能认定行为人构成贪污罪。如果仅仅因为行为人无力证明财物的去向就认定为贪污,实质上是要求行为人自己证明没有实施贪污行为,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违背。
具体到李某某贪污一案,笔者认为从无罪推定的角度,李某某是无罪的。
李某某取得公款的行为合法,其行为是否构成贪污关键在于其是否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本没有支出,或为其个人事务支出的款项用伪造领导签名、使用虚假票据报销、重复报销票据等方式平账。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检察机关要指控李某某贪污公款,至少要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两点:
①该公款李某某没有支出或已为其个人事务支出;
②李某某有贪污的故意。其用伪造领导签名、使用虚假票据报销、重复报销票据等方式平账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其将公款占为己有的事实。但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显然证明不了以上两点:
一
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证明李某某有贪污的故意,甚至连李某某贪污的故意是什么时候产生的都无法回答。
首先,毋庸置疑,肯定不能认定李某某从某办会计处借取现金时就有贪污的故意。因为借取现金后保管及使用是出纳李某某的职责,这种管理模式尽管不太符合财务管理制度,但在某办一直是这样执行的。
其次,那么李某某的贪污故意是产生于其伪造领导签名、使用虚假票据报销,重复报销票据之时吗?当然不是!因为李某某这样做有客观原因:其账目管理混乱,很多支出没有及时记账,没有妥善保管支出凭证,某办领导又因特殊原因对此事消极处理。所以在审计部门审计出李某某的短款11万余元后,李某某为了自己不承担这个损失不得已才采取了上述手段,并非为了实现非法占有该11万余元的目的。事实上,李某某采取上述手段欲平账的11万余元中,有8.7万元确实实际为公支出,审计部门,检察机关、一审法院也认可这一部分不应认定为贪污。剩余的2.3万元被认定为贪污只是辩方提供的涉及该部分款项的证据未能被一审法院认可——但检察机关也不能提供证据排除该2.3万元被用于公务支出的可能。所以,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要李某某采取了伪造领导签名、使用虚假票据报销,重复报销票据等行为平账就有贪污的故意,要看其实施这些行为的主观目的。
第三,李某某的贪污故意是审计部门审计完毕之后,李某某既找不出为公支出6.6万元的凭证,也没有补交该6.6万元之时吗?当然也不是!审计完毕之后,并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要求李某某将其不能提供支出凭证的短款6.6万元上交某办,某办与李某某之间没有对短款部分如何处理进行过协商,李某某也没有表示过拒绝补齐上述短款,又何来非法占有的故意呢?况且,进入诉讼程序后,李某某又提供证据证实起诉书指控的6.6万元贪污数额实际为公支出了,其中4.3万元为一审法院认可。
最后,更不能凭李某某的供述认定其有贪污的故意。不断出现的为公务支出的证据充分证实李某某的供述是靠不住的,而且第一次讯问之后李某某已完全否认自己占有了涉案款项。
二
检察机关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2.3万元李某某没有支出或该2.3万元李某某为其个人事务支出,不是为公支出。如果有,那就是李某某第一次的有罪供述。但其供述如前所述并不客观,不能证明2.3万元被其占为己有。
在无法证明李某某有贪污故意的情况下,如果将李某某供述已经为公支出,但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实的2.3万元认定为其贪污的数额,这实际上不是由检察机关提供证据,排除其他合理怀疑证实李某某用侵吞、窃取、骗取或其他的方法实施了非法占有该2.3万元的行为,而是由李某某提供充分、确凿证据证明自己没有用侵吞、窃取、骗取或其他的方法实施了非法占有该2.3万元的行为,证明自己无罪!这与无罪推定原则确定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不负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相悖。
有罪推定目前刑法中只有一个罪名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包括贪污罪在内的其他罪名并不适用。
同样基于无法证明李某某有贪污的故意以及李某某已将2.3万元占为己有这两个理由,笔者认为,即使审计局审计以后,李某某以该笔款项已为公支出为由不想承担损失,拒不补交短款,也不能将其行为认定为贪污——除非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李某某确实将该款项非法占为己有,排除该款项已为公支出的可能,但李某某却编造已为公支出的借口拒不归还。解决某办与李某某之间争议的正确方法是某办应当要求李某某提供已为公支出的支出凭证平账。在其不能提供支出凭证时,某办可以责令李某某补交短款,甚至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李某某将短款补齐——因为李某某从会计处领取公款是事实,现在因为其本人的原因不妥善保管支出凭证,没有将账目记录清楚,又不能证明款项已为公支出,导致短款,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通过行政或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李某某对某办短款的问题,而不是追究李某某的刑事责任,这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