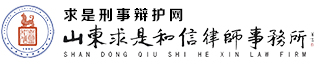【人民法院案例库】聚众斗殴罪裁判要旨(7例)
目录:
1.如何区分多人故意伤害与聚众斗殴行为
2.聚众斗殴中既致人死亡又致人轻伤的定罪处罚
3.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如何认定
4.未成年人陪同前往殴斗现场,未实施实质殴斗行为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5.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案件的处理规则
6.共犯实行过限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责任认定
7.互殴型聚众斗殴中共同犯罪的审查认定
1.李某等故意伤害案——如何区分多人故意伤害与聚众斗殴行为
【参考案例】
入库编号:2023-04-1-179-004
入库日期:2024.02.22
【裁判要旨】
在司法实践中,要准确区分多人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与聚众斗殴行为的性质,需要在犯罪客体、主观方面等进行精准把握。聚众斗殴罪的犯罪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行为人主观心态上一般是出于为了争霸一方抢占地盘,或为了报复他人,或为了寻求刺激等公然蔑视国家法纪和社会公德的犯罪动机;故意伤害罪的犯罪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主观方面一般是伤害他人的故意,犯罪动机可能多种多样。
2.王某某故意杀人案——聚众斗殴中既致人死亡又致人轻伤的定罪处罚
【参考案例】
入库编号:2023-05-1-177-012
入库日期:2024.02.21
【裁判要旨】
1.聚众斗殴转化定罪,不仅要考察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否由一般斗殴转化为故意伤害、杀人的故意,还要考虑行为人是否实行过限,超出了聚众斗殴的界限,造成了他人重伤、死亡后果。聚众斗殴既致人死亡,又致人轻伤的,是认定为故意杀人一罪还是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两罪并罚,在司法实践中有不同认识。从对法条的理解上看,对于聚众斗殴致人轻伤、轻微伤的,仍认定为聚众斗殴罪,排除了转化为故意伤害罪的可能。从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上看,聚众斗殴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不确定的概然性故意,聚众斗殴致人轻伤的行为并没有超出聚众斗殴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之外。故,对于聚众斗殴中既致人死亡又致人轻伤结果的,应按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转化定罪,以故意杀人罪一罪定罪处罚即可。
2.聚众斗殴转化定罪主体范围认定问题。审理聚众斗殴转化定罪案件,应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考量行为人在聚众斗殴中的作用、地位,依据共同犯罪的规定,具体确定转化的主体范围。对超出共同犯罪故意范围“实行过限”的被告人,应当根据罪责自负原则由其个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3.刘某惠、胡某等聚众斗殴案——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如何认定
【参考案例】
入库编号:2024-04-1-268-001
入库日期:2024.11.25
【裁判要旨】
1.恶势力集团犯罪中,犯罪分子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较少,但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与他人经常纠集系为共同实施违法犯罪,仍按照纠集者的组织、策划、指挥参与的,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
2.由恶势力犯罪集团部分成员实施的违法犯罪,首要分子事后赔偿对方损失、安排人员报复对方或者安排己方人员道歉的,应当认定为犯罪集团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首要分子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3.为斗殴实施了聚众行为,因对方未赴约没有实际实施斗殴行为的,属于聚众斗殴未遂。
4.唐某甲、唐某乙故意伤害案——未成年人陪同前往殴斗现场,未实施实质殴斗行为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参考案例】
入库编号:2024-02-1-179-003
入库日期:2024.02.25
【裁判要旨】
未成年人受他人纠集参与聚众斗殴等犯罪的,要综合其动机、行为性质、行为积极性、参与程度、危害后果、归案后表现等情况,坚持对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为原则,审慎把握定罪及量刑。如果整体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影响不大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
5.钱某、葛某故意伤害案——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案件的处理规则
【参考案例】
入库编号:2024-04-1-179-005
入库日期:2024.02.24 / 修改日期:2024.07.10
【裁判要旨】
1.对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转化适用故意伤害罪,应当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要求,结合案件具体事实,在准确认定行为人主观方面的基础上作出妥当处理。
2.对于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应当按照其所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聚众斗殴出现重伤后果,构成故意伤害罪的,无论首要分子是否实施直接造成重伤的行为,均应依法转化适用。
6.张某军故意杀人、张某明等人故意伤害案——共犯实行过限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的责任认定
【参考案例】
入库编号:2023-04-1-177-023
入库日期:2024.02.22 / 修改日期:2024.02.26
【裁判要旨】
1.对于共犯实行过限的认定,裁判者对有关行为主体、行为时间、主观罪过等因素的判断较为容易,但往往难以把握“行为是否超越共同谋议之罪范围”这一核心问题,司法实践中,应以“共同谋议”这一概念作为判断核心,从以下三个方面重点把握:
一是共同谋议的内容明确,各共同犯罪人就犯罪目标、手段、程度等已经达成了具体详细的合意,形成了统一的行动方案。在此情况下,如果各行为人都能够按照事先谋议的内容实施犯罪,则将在共同谋议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如果其中部分实行行为人实施了超过谋议范围的事项,一般可认定为共犯实行过限。
二是共同谋议的内容并不明确,反而呈现出明显的概括性,即实行犯之间以“教训教训”“收拾收拾”之类的语言达成合意,在实施过程中则表现为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此类情况下,实行犯的行为只要不是明显超出共同谋议范围,都应视为整个共同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宜认定为实行过限。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裁判者需结合具体案情准确把握概括性合谋的边界,避免过分扩大解释。
三是各共犯人在事前或事中缺乏明显的共同谋议,而是通过实际行动、神态表情等进行犯意联络,该种情况在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犯罪中较为常见。共同犯罪人往往先因故与被害人产生口角或纠纷,在矛盾突然激化后实施暴力行为。由于事态变化迅速,各共同犯罪人无暇进行直观的犯意联络,故较难认定行为是否超过共同谋议范围。对此,宜结合实行犯的组织地位以及多数行为人行为方式等因素综合进行判断。如果行为人以明显超越多数共犯人行为性质、手段、程度的方式实施犯罪行为,一般可认定为超过共同谋议范围。
2.对于共犯实行过限情况下各共同犯罪人归责问题的判断,宜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要从客观上判断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是否明确。过限行为往往会造成比共同谋议的犯罪目的更为严重的法益侵害后果,此时需判断该严重危害后果的成因是否明确。对于以上问题的判断有必要区分重合过限之罪与非重合过限之罪。基于非重合过限之罪与共谋之罪在侵害法益性质方面的明显区别,相关责任归属相对明确,一般应由过限行为人单独承担过限行为的刑事责任。由于重合过限之罪与共谋之罪在所侵害的法益上具有相似性,实践中尤其需要解决的是对重合过限之罪的责任承担问题。如果根据在案证据,致害成因不能精准指向某具体行为人,即使存在共犯实行过限,一般也不宜将过限行为人与非过限行为人分别定罪论处,应当要求共同犯罪人整体对危害后果负责。如果在案证据能够证明致害结果是过限行为人直接造成的,过限行为人需对该结果负责在所不论,非过限行为人是否应承担责任需结合具体案情进一步分析判断。
二要从客观上判断非过限行为是否为过限行为的实施创造了条件。在致害成因能够精准指向某非过限行为人时,在部分共同犯罪尤其是非重合过限之罪中,首先需要判断非过限行为与严重危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过限行为人完全是另起犯意的,非过限行为与严重危害后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相反地,在部分共同犯罪尤其是重合过限之罪中,非过限行为致使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境地,过限行为人基于此再行实施过限之罪的,则非过限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要从主观上判断非过限行为人对过限行为是否具有预见可能性。在致害成因能够精准指向过限行为人时,非过限行为人只有符合因果关系要求,且对危害后果具有预见可能性才能承担责任。如果非过限行为人缺乏事前及事中的明知,且在一般情况下,不具有可预见性,则不对过限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7.李某坤、王某豪、张某鹏聚众斗殴案——互殴型聚众斗殴中共同犯罪的审查认定
【参考案例】
入库编号:2025-05-1-268-001
入库日期:2025.06.07
【裁判要旨】
对于互殴型聚众斗殴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应当结合主观故意、犯罪对象、犯罪目的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互殴的双方虽然共同实施了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但双方的犯罪对象不同,犯罪的主观故意不同,不应将互殴的双方认定为共同犯罪,而应当对双方犯罪分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