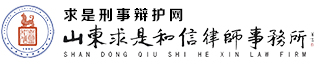于某亭制造毒品罪辩护词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上诉人于某亭亲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在征得于某亭本人同意后,继续为于某亭辩护。辩护人是于某亭的一审辩护人,对本案事实已全面掌握,现结合一审判决书,发表如下三个部分的辩护意见:
第一部分 一审判决书认定“于某亭通过网络查阅资料,掌握了制造毒品的工艺……购买制毒工具……废弃厂房内非法制造甲卡西酮……于某亭为改进自己的制毒工艺,经常在网上向曾制造过毒品的被告人刘东京请教,并邀请刘东京来山东共同制造毒品”完全与事实不符。认定上诉人于某亭犯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不能成立。
一、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就是为了生产毒品、让刘东京来山东昌邑市就是为了共同生产毒品、以及于某亭明知其生产、贩卖的的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甲卡西酮证据不足,显属认定事实错误
1、于某亭从未供述自己生产的目的是制造毒品甲卡西酮;未供述自己知道生产的中间产物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毒品甲卡西酮;未供述刘东京来山东昌邑市是为了共同生产毒品。于某亭整个诉讼阶段一直比较稳定的供述就是其通过互联网学习生产麻黄碱的工艺,并购买了设备、原料实际投入生产麻黄碱;于某亭进行到制作出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这一步后,后面的步骤没有成功,使用中间人“a-”提供的原料溴代苯丙酮也没有试验成功,制作出麻黄碱;因为刘东京懂“麻黄素”生产技术,想与于某亭合伙干,于某亭同意后刘东京遂到昌邑;看了生产场所后,刘东京嫌生产溴代苯丙酮味道太大,受不了,改为生产氰基苯丙酮这种制作冰毒的中间体;于某亭、刘东京购买了原料生产氰基苯丙酮,但是也一直没有试验成功;为了回本,筹集资金继续试验生产氰基苯丙酮,在中间人“a-”得知其放弃生产麻黄碱后,提出收购其制做麻黄碱的中间产物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于某亭遂将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卖给中间人“a-”。
2、刘东京从未供述其与于某亭讨论过生产毒品甲卡西酮的问题;未供述其到昌邑市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于某亭共同生产毒品甲卡西酮;未供述告诉过于某亭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就是毒品甲卡西酮,于某亭知道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就是毒品甲卡西酮。刘东京供述其与于某亭通过QQ交流的是用化学原料制作溴代麻黄碱的话题;于某亭告诉刘东京自己购买了原材料及器皿尝试制作麻黄碱,但因为在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提纯步骤上遇到了困难,制作麻黄碱进行不下去了,才邀请刘东京到昌邑市一起寻找解决的方法或者制作其他的“化学中间体”;于某亭与刘东京购买了生产氰基苯丙酮的原料,试验制造氰基苯丙酮,但一直没有试验成功。
需要提请合议庭注意的是:结合本案的证据,刘京东所说的其他的“化学中间体”可以确定指的是氰基苯丙酮这种制毒中间体,而不是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这种被称为甲卡西酮的新型毒品。
3、于某亭对其生产麻黄碱工艺流程的供述,完全符合利用溴代苯丙酮化工合成麻黄碱的反应途径及生产工艺:先生产溴代苯丙酮,之后加入甲胺生产出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再经过拆分“消旋体”,用硼氢化钾还原就生产出麻黄碱了。现场查获的硼氢化钾、酒石酸印证了于某亭生产出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后为继续进行拆分反应和还原反应所做的准备,现场查获的的红色胶状物印证了于某亭进行了拆分和还原反应为试图制作麻黄碱所做的努力。
4、现场查获的乙酸乙酯等原料,印证了于某亭在无法生产出麻黄碱后,采纳刘京东的建议,改为生产另一种制毒中间体——氰基苯丙酮的事实。
5、因为考虑到溴代苯丙酮纯度不够可能是于某亭不能成功制造出麻黄碱的原因,中间人“a-”曾为于某亭提供过一瓶溴代苯丙酮进行试验,但于某亭仍然没有试验成功。知道于某亭无法生产出麻黄碱后,“a-”才提出购买于某亭生产的中间产物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但并未告知于某亭其购买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的用途。于某亭卖给中间人“a-”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的价格(3000元/公斤)远远低于毒品甲卡西酮市场交易价格也能印证于某亭并不知道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可以作为毒品使用,于某亭是作为麻黄碱中间产物销售,而不是作为毒品甲卡西酮销售的事实。
6、于某亭通过中间人“a-”销售其生产麻黄碱的中间产物胺盐,并在第三次用石膏粉欺骗买方,将中间人“a-”从联系人中删除的行为,印证了于某亭的目的并不是生产并销售甲卡西酮,其行为只是因为不再生产麻黄碱这种制毒中间体,转而生产另一种制毒中间体氰基苯丙酮,为了回笼资金,而将试制麻黄碱的中间产物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卖掉的事实。当然,中间人“a-”要压低价格获取高额利润,不告知于某亭其出售的中间产物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毒品甲卡西酮自在情理之中。
7、一审判决以“于某亭通过网络学习制毒技术多年……所查扣的液体中含有甲卡西酮”为由,认定于某亭主观上对于生产、出售的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毒品甲卡西酮应是明知的缺乏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1)于某亭供述其研究的是麻黄碱的制造技术,从未供述过其研究的是制毒技术;
(2)前已述及,不管从于某亭购买的原料还是现场查获的物证,都证实于某亭目的是想制作麻黄碱的供述是真实可信的;
(3)在百度上输入“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字样查询,不会出现甲卡西酮的相关信息。《公安部对河南省禁毒总队就崔艳云一案提取的“a-”甲氨基苯丙酮盐酸盐是否为甲卡西酮的请示答复》的主要内容为:你总队请示的“甲氨基苯丙酮”分子式、化学结构与甲卡西酮均一致,因此,两者是同一物质。但对该答复的具体内容,不管是通过百度搜索引擎,还是在专业法律法规检索软件如《北大法宝》、《Alpha》、《威科法规》上都检索不到。只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豫法刑一终字第48号崔艳云等人贩卖毒品二审刑事裁定书搜索到该答复的内容。所以,仅凭初中都未毕业的学识,没有毒品犯罪前科的于某亭,仅仅根据其在网络上学习制作麻黄碱技术多年推定其知道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就是毒品甲卡西酮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
(4)于某亭自己知道制造、买卖麻黄碱也是犯罪行为。因此,不能依据于某亭交易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时的秘密性等就认定于某亭明知自己交易的是毒品。
如果认定于某亭行为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做和贩卖毒品甲卡西酮,那么他的很多行为就不符合常理,难以解释:
1、既然已经制造出了毒品甲卡西酮,为什么还要购买用于拆解和还原反应的原料,并进行下一步的试验?如果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未雨绸缪,为了掩饰案发后被追究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刑事责任,似乎有点考虑太缜密、太不可思议。
2、既然目的是为了制造毒品,也已经制造出了毒品甲卡西酮,并有了销售渠道,为什么要停止生产,转而生产另一种制造毒品的中间体氰基苯丙酮?并且把已经建立的销售渠道主动破坏?
3、既然于某亭知道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毒品甲卡西酮,也将其作为毒品销售,为什么销售的价格远远低于甲卡西酮这种毒品的市场价格?
综上,本案两上诉人的供述、于某亭购买的原料、反应生成物、于某亭出售假的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以及于某亭出售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的价格等能够相互印证,证实于某亭本想生产麻黄碱销售牟利,但未能成功,在刘东京的建议下,转为生产氰基苯丙酮,在中间人的提议下,于某亭为了回笼资金,将生产麻黄碱过程中的中间产物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销售,但其只知道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生产麻黄碱的中间产物,并不知道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毒品甲卡西酮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的行为就是为了生产毒品,刘东京到山东昌邑市就是为了和于某亭一起生产毒品,以及于某亭明知其生产的中间产物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甲卡西酮而予以贩卖明显与事实不符,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一审判决认定的其他事实亦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本案侦查机关在物证的提取、扣押、称量及取样的过程中程序严重违法,所取得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依法应予排除
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四条、第五条,涉案毒品应当在有犯罪嫌疑人在场并有见证人的情况下,当场提取、扣押。毒品的提取、扣押应当制作笔录,并当场开具扣押清单,扣押的涉案毒品应按《公安机关缴获毒品管理规定》规定的程序和地点集中统一保管。
本案中,2017年6月3日案发,6月4日公安机关对位于昌邑市北孟镇初家上疃村村西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但扣押清单却制作于2017年6月14日,扣押地点是济南市历城区凤歧路停车场,从案发到扣押长达十天之久。公安机关提取物证时既没有制作提取笔录,将物证从昌邑转移至济南也没有见证人。从齐鲁网公开报道的新闻中可知,济南公安机关从2016年12月到2017年10月,破获了建国以来山东省规模最大最复杂的网络制毒、贩毒案件,查获了大量的甲卡西酮等毒品,本案是这起毒品窝案中的一起。所以,本案在提取和转移的过程中,上述物证以及毒品有没有发生变化?有没有被污染?有没有与其他的毒品混同?有没有其他人为的因素?这些合理的怀疑都不能排除,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
2、根据《规定》,毒品的称量一般应当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在查获毒品的现场完成。不具备现场称量条件的,可以带至公安机关办案场所或者其他适当的场所进行称量。本案中,案发现场具备称量条件,但侦查机关没有合法理由在济南市历城区凤歧路停车场进行称量。辩护人查看称量视频发现,称量时,并未显示侦查机关按《规定》要求将衡器示数归零,也未让于某亭当场在称量笔录上签名,而是在看守所让于某亭在称量笔录上签名。
3、根据《规定》,毒品的取样一般应在称量完成后,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在查获毒品的现场或者公安机关办案场所完成。但本案的取样笔录上虽然载明的取样地点是在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分局鲍山派出所,但从称量视频中可以发现实际取样是在济南市历城区凤歧路停车场称量的过程中完成。对于抽取液态检材的数量,《规定》明确要抽取二十毫升,但抽样笔录中却未记载抽取检材的数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4、《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进行含量鉴定的检材应当与进行成分鉴定的检材来源一致,且一一对应。这里规定的来源一致,不是说要用同一个检材。而《济南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理化检验报告书(济)公(刑)鉴(化)字[2017]377号》和《济南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理化检验报告书(济)公(刑)鉴(化)字[2017]365号》委托检验的时间和出具报告的时间都是不同的。但两个报告书却共用检材2-1红色液体和2-2液体。检材的数量是否达到检验要求?检材是否被污染?这些怀疑都不能得到有效排除,如此检验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守法公正。
同时,证据的合法性要求鉴定机构中的鉴定人应当符合法律的规定的要求。该检验报告书的鉴定人是马广鹏,而马广鹏也是本案的专家证人,为警方提供了咨询意见。根据《公安机关鉴定规则》第三章第十条的规定,马广鹏应当回避而不应该作为鉴定人出具检验报告。
5、本案中,尽管扣押、称重、取样的地点和时间都是不同的,但唯一不变的就是见证人都是王伟,王伟有“职业见证人”的嫌疑。公诉机关提供侦查人员自己的说明以及一份没有提供人签字及盖章的合同复印件,显然不能证明王伟就是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的职工。况且,济南振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劳务派遣公司,该合同复印件亦不能证实王伟具体被派遣到哪个公司以及是否还在该公司工作。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王伟是合法的见证人。所以,由王伟见证的相关扣押、称重、取样程序违法,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综上,上述物证、理化检验报告书等证据,因提取、扣押、称重、取样、检验程序违法,导致某些事实无法认定,可能影响司法公正,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一审判决对辩护人依法提出的本案证据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未作出相应的回应,直接作为定案证据采纳,有失客观公正。
(二)于某亭、付远刚、武继状的供述互相矛盾,也与本案的其他证据相矛盾
1、案发后第三天,也就是2017年6月6日,于某亭供述的非常清楚:三次交易中,第三次是用石膏粉代替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里面没有掺砖头。买方第一次开的是一辆黑色宝马,第二次是一辆白色的奔驰GRA,第三次是一辆奥迪Q7,其中第一次和第三次还用手机进行了录像。于某亭供述的买方所开车辆的型号、颜色都非常清楚、确定。我们可以看出,整个诉讼阶段,于某亭对整个案件事实均如实供述,没有避重就轻,也没有反复。辩护人看不出于某亭单独在买方所开车辆这一事实上做虚假供述的动机和必要。因此,于某亭的这一供述是真实可信的。
2、2017年10月9日制作的付远刚供述笔录中,付远刚先供述其通过“龙家三少”联系从“九道”处花费150万元购买了甲卡西酮200公斤,从“小二”武继状和“小四”胥林亚处分四次共计购买甲卡西酮45公斤,与武继状一起从高密购买了20公斤实际是石灰粉的假甲卡西酮,但唯独没有供述起诉书指控的从高密分两次购买的共计9.5公斤甲卡西酮。直到2017年10月10日的第六次供述笔录中,付远刚才供述其通过“龙家三少”从高密购买过三次甲卡西酮:第一次是自己独自去高密购买了4.5公斤甲卡西酮;第二次是与武继状去高密购买了不到5公斤甲卡西酮;第三次是与武继状去高密购买甲卡西酮20公斤,结果被骗,买到的了一袋石粉,里面有两块砖头。这三次付远刚都是开自己深色的宝马X5越野车去的。其中,付远刚第二次支付“龙家三少”12万元欲购买的是15公斤甲卡西酮,但最后只有不到5公斤。
3、武继状在其前五次供述笔录中详细供述了其参与与付远刚一起购买甲卡西酮六次,数量至少在890公斤以上,但未供述与付远刚去高密购买甲卡西酮的事实。2017年10月13日的第六次供述中才供述与付远刚去高密购买甲卡西酮被骗,买到的甲卡西酮是土和砖头的事实,但仅仅供述了这一次,并未供述起诉书指控的第二次交易是其与付远刚去的高密。
4、于某亭供述三次交易都是通过网名“@-”,QQ号为3408755263的中间人交易,而付远刚供述是通过网名“龙家三少”,QQ号码为3516448377的中间人交易。于某亭与付远刚所供述的中间人的网名和QQ号码都是不同的。侦查机关的《工作说明》说明中间人邓炜华在逃,而梁军胜证实其用这个3516448377的QQ号骗过一次付远刚后将其转让给邓炜华。邓炜华又用这个QQ号再骗付远刚,且又骗了两次。
从辩护人列举的上述上诉人供述等证据中,我们可以看出本案存在以下疑点:
1、于某亭的供述自始至终客观、稳定,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反观付远刚、武继状的供述,对于本案事实的供述从一开始的没有供述,到以后的逐渐供述,与于某亭的供述有趋同的趋势,但最终还是存在严重的矛盾。起诉书指控的交易甲卡西酮的数量不到10公斤,在付远刚、武继状一开始就供述的他们交易的甲卡西酮数量800多公斤中可以认为可忽略不计,但为什么他们在第五、六次供述中才开始供述去高密购买甲卡西酮的事实?且在交易的中间人是谁、购买甲卡西酮的人所开的车辆、第二次付远刚是自己去的高密还是与武继状一起、第三次被骗购买的假甲卡西酮石膏粉中有没有砖头等事实上供述还存在着严重矛盾?
2、按照付远刚的供述,其第二次去高密购买甲卡西酮就在数量上被骗,为什么还要那么容易第三次再被骗?按照梁军胜的证言,其用3516448377的QQ号骗过一次付远刚,然后转给邓炜华,邓炜华又用这个QQ号骗了付远刚2次?付远刚为什么那么容易受骗?真的是因为付远刚钱多人傻?这真是让人无法理解。
3、正如辩护人在一审法庭调查阶段所指,起诉书指控的于某亭诈骗罪的犯罪数额与本案侦查机关调取的于某亭支付宝的收款记录不能相互印证。侦查机关既然已经调取了上述交易记录,但为什么不调取于某亭与中间人、付远刚与中间人钱款往来的记录呢?
本案移送审查起诉后,公诉机关应该注意到了证据之间的矛盾,所以制作的于某亭的讯问笔录模糊了买毒人所开的车辆(但于某亭的当庭供述与原在侦查机关的供述是一致的),付远刚和武继状的供述笔录也不再提及购买的假毒品中掺有砖块。一审庭审中公诉人认为这些矛盾只是一些细节,不影响其供述的真实性,但辩护人不敢苟同:
首先,这些矛盾并不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其次,我们分析付远刚、武继状供述的真假,应放在整个案件中综合考量。辩护人注意到于某亭是2017年6月份供述在先,付远刚、武继状2017年10月份供述在后,且付远刚、武继状犯罪情节非常严重,按期其供述的贩卖甲卡西酮的数量,应处死刑,他们有配合司法机关的动机。
综合分析本案证据,辩护人认为本案现有证据不能排除付远刚、武继状的供述是虚假供述的可能,不能得出付远刚就是购买于某亭销售的甲卡西酮买主的唯一结论。如果排除以上证据,辩护人认为本案认定上诉人于某亭贩卖、运输毒品的定罪证据仅有上诉人的供述。而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仅有上诉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上诉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但一审判决无视上述证据中存在的证据合法性等问题,无视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未经调查核实直接将其作为定案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依据这些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只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在确定于某亭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毒品甲卡西酮,其也不明知自己销售的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就是毒品甲卡西酮的前提下,剩下的问题就是:于某亭有制造和贩卖制毒物品麻黄碱的故意和行为,虽然其不明知制造麻黄碱的中间产物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新型毒品甲卡西酮,没有制造和贩卖毒品的故意,但其客观上制造和贩卖了毒品甲卡西酮,这一行为如何定性?是认定为制造、贩卖毒品罪,还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简而言之,焦点问题就是:于某亭对事实的认识错误能否影响到对其行为的定性?
辩护人认为,在对于某亭的行为进行定性时,仍然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因为于某亭不知道其制造、运输、贩卖的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毒品甲卡西酮,没有制造和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不应认定其构成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对事实的认识错误分为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和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
具体的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认识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虽然不一致,但没有超出同一犯罪构成的范围,即行为人在某个犯罪构成的范围内发生了对事实的认识错误,因而也被称为同一犯罪构成内的错误。对于具体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我国刑法理论采用“法定的符合说”,即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只要在犯罪构成的范围内是一致的,就成立故意的既遂犯。比如,甲某本欲杀害乙某,在黑夜里误将丙某当成乙某杀害。甲的行为属于对象错误。根据“法定的符合说”,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想杀人,而客观上又实施了杀人的行为,那么就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既遂。所以,在杀死丙的事实范围内,甲的行为主客观一致,甲成立故意杀人罪既遂。
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现实所发生的事实,分别属于不同的犯罪构成;或者说,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与所发生的事实跨越了不同的犯罪构成,因而也被称为不同犯罪构成间的错误。
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在责任主义原则基础上,以法定符合说为标准判断故意的成立,即在主观故意与客观事实的法律评价相一致的范围内认定是否成立故意犯罪。
1.行为人主观上想犯轻罪,客观上却触犯重罪。如果客观事实在法律评价上包含轻罪的客观事实,则按照轻罪的故意犯罪既遂处理。该种情形不可能成立重罪的故意犯罪既遂,因为行为人没有认识到重罪的客观事实,没有犯重罪的故意(但对重罪事实可能成立过失犯罪,属于想象竞合犯)。
2.行为人主观上想犯重罪,客观上却发生轻罪的结果。如果主观故意在法律评价上包含轻罪的故意,那么,根据案件具体情形确定是否成立重罪未遂。这种情形有两种处理结论:
(1)当案件存在重罪的实行行为,并导致重罪的危险结果时,则成立重罪未遂,同时也成立轻罪(既遂),认定为重罪未遂与轻罪(既遂)的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处罚。
(2)如果没有重罪的实行行为,也没有重罪的危险结果,则不成立重罪未遂,只是成立轻罪(既遂)。
生产、运输、销售甲卡西酮构成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没有争议。但本案中,于某亭不知道自己生产麻黄碱的中间体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是毒品甲卡西酮,为了回笼资金,仅仅是将其作为制作麻黄碱的中间体销售,而不是作为毒品甲卡西酮销售。而买卖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这种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构成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对此于某亭也是明知的。买卖毒品甲卡西酮和买卖制毒物品甲胺基苯丙酮盐酸盐都构成犯罪,但两者显然属于不同的犯罪构成,相比较而言,前者属于重罪,后者属于轻罪。所以,本案于某亭的行为属于事实认识错误中的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对其行为进行定性时,按照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应当在主观故意和客观事实的法律评价相一致的原则范围内,认定其成立轻罪的犯罪既遂,而不是重罪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既遂,即于某亭的行为不能认定为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
在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也就是本案于某亭的行为定性中,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处理原则,也为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判决所认可:
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2015)滨刑初字第153号刑事判决书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岩刑初字第19号刑事判决书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赣中刑一初字第39号刑事判决书
上杭县人民法院(2016)闽0823刑初214号罗华生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锡刑二初字第00018号刑事判决书
江西赣州中院审理的(2015)赣刑三终字第47号廖忠伟等人制造毒品甲卡西酮案
第二部分 起诉书指控上诉人于某亭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前已述及,对于于某亭第三次交易的事实,买方所驾车辆、假毒品中有无砖块,于某亭、付远刚、武继状的供述互相矛盾,公诉机关也未提供付远刚付款的证据,认定付远刚就是于某亭诈骗案的被害人证据不足。侦查机关调取的于某亭支付宝收款的记录也与于某亭的供述以及起诉书认定的数额不能相互印证。因此,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上诉人于某亭犯诈骗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第三部分 一审法院无管辖权,审理本案程序违法
本案起诉书指控的于某亭制造、运输以及与付远刚交易毒品均没有发生在潍坊市,于某亭的居住地也在潍坊市。刘东京以及付远刚的居住地都不在济南市,济南市也不是本案的犯罪地。根据刑事诉讼法以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只能由潍坊市公安机关或付远刚居住地聊城市公安机关管辖。辩护人认为:山东省公安厅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指定本案由济南市公安机关管辖,但对于本案有什么特殊情况必须指定济南市公安机关管辖未予充分说明,属滥用指定管辖,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案件管辖的规定,程序违法。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审议。
辩护人: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 李宗习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